提要 Overview
时间:2018-05-02 14:41 三联《爱乐》 nolix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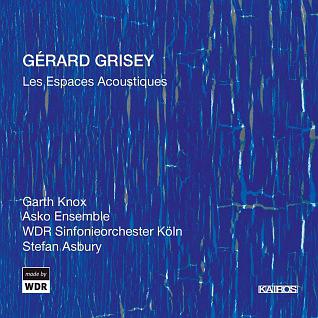
刊载于2017年 三联《爱乐》 4月刊
众声纷杂,融人阴暗之寂静中。寂静乃无限之空间也。灵魂迅疾而沉默地飘浮于世世代代生息不已之空间。灰色薄暮弥漫于此,却从不落到暗绿色之辽阔牧场上。仅降下苍茫暮色,抛撒星宿的永恒之露。
—— 乔伊斯《尤利西斯》
一
谈到最近十几年的当代作曲界,频谱乐派恐怕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然而所谓“频谱”究竟是指什么呢? 正学着电子音乐制作的朋友二话不说,将我拉到了电脑屏幕前。果然,示例再形象不过:倘若仔细观察,他手头编辑着的小提琴声,在电脑软件的频率波表一栏形成了蛋糕状的层叠图形——又像是石子投入湖心的水波纹,只是在频率越高的地方,波纹的间隔越小罢了。一般而言,当琴弓迅速离开琴弦时,振动会立即消失,振幅线条也会形成迅速衰减的趋势。 这就是图像化后的基音-泛音频率规则,自然界之声响,亦不能例外。早在古希腊,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就研究过乐器发音中的数学规律。传说里是这样的:毕达哥拉斯听到打铁声时,注意到有些击打声音的组合格外悦耳。他便仔细观察铁锤,发觉一个重12磅,另一个重6磅,正好形成倍数关系。事实证明,几乎所有的乐器都能吻合震动频率成比例的原则,譬如两个乐器同时演奏出的振动频率是较为简单的比例关系时(如1/2或3/2), 声音是明显和谐的。两件乐器如此,而在同一件乐器上的和谐音色,莫不也是由多层次的频率组合而成,譬如刚才提到的小提琴。小提琴上还能单独奏出自然(单指轻触弦)与人工泛音(双指虚实同按) ,一般到基音的第三、四“级”就已相当可观;吉他六根弦上能发出清晰自然泛音约有二十个左右,而超高把位上的准度是不太高的;我们自己的民族乐器间,扬琴的清透泛音是以中指指尖浮点轻触所击琴弦获得的。 作曲范畴内所讨论的“频谱”,笼统说来就是将声音频率的规律客观化与数学化。请留意,下文采用的是“泛音”这一译法。实际上我们说的第一“泛音”就是指第二“谐音”,第二“泛音”即第三“谐音”,以此类推。玛丽.克莱尔.缪萨的《二十世纪音乐》书对这一学派的基本特征总结得较为简洁:“由具有声学属性的材料构成的音乐,就称作频谱音乐。”可以说,正是基于了对声音基本属性的认识,法国作曲家们创立了轰动一时的频谱学派。

杨珽珽所作的《法国频谱音乐简介》一文,优美地形容该学派的思想渊流:“作曲家发现,声音的参数决定了其波动或显得模糊的特征,就像一部置于一组声音'光影对比'之下的作品。从谐波分布、泛音的相对强度,到声音的组合和波动,这些都给予每一个或每一组声音独有的氛围。 ” 理论方面,频谱音乐的音高结构一般基于泛音音列(有时甚至是每个八度按照等差关系缩放形成的“非八度循环”谐音列)那是按弦长比例产生的音高关系,所以更加接近纯律。特别是较高泛音上的微分音,在十二平均律中无法做到。在整个泛音列中,基音一般被强调得程度最大,此是其一;前几个泛音的关系基本是四五度,但越往后越会出现微分音,到了32号泛音后就出现了八分之一与十六分之一的音高,频谱密度越来越大,而音响就愈加地不和谐,这是其二;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共振峰。每个泛音内部都一个最高响度的区域,取其音量的顶峰值就是共振峰,它直接决定了泛音的音色,继而决定了音响的面貌。在实际操作中,频谱作曲家往往热衷于按照泛音列的共振峰比例来设计与安排各声部的音高关系。如此一来,音乐从本质上成为了一门最接近数学的艺术——可能比绘画要接近得多,因此足以基于物理学的算法、依托电子技术的实践自成一统。

现在,应该轮到本文的主人公杰哈尔•格里塞出场了。他是频谱乐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尽管在他之前,五花八门的记谱法已经遍布世界,但也许只有格里塞,才让我们真正地意识到传统谱曲思维早已不代表音乐与音乐创作的唯一存在形式。1946年,格里塞生于靠近法、瑞边境的贝尔福特,年轻时做过梅西安和杜蒂耶的学生,也去1972年的达姆施塔特参加过当代音乐进修班,跟随泽纳基斯和利盖蒂学习过作曲。他80年代任教于美国伯克利,晚年回到了巴黎。 实际上,格里塞并不是一个天生的频谱主义者。1939年生的英国作曲家哈维(Jonathan Harvey)在他之前就倡导过“色彩分析法”——他的焦点在于音色本身,比如认为瓦格纳等人才是频谱运动的真正先驱,但哈维这么解释有将问题简单化之嫌。到了1973-74年,格里塞写出了著名的《漂移》(Dérives,与布列兹作品同名),一部为两组乐队而创作的作品,才标志着他对序列音乐语言和美学观的彻底宣战,走入了“创作音色声音时代”。可是《漂移》和《异音》(Heterophonie)仍旧没有放弃使用传统和声作为伴奏素材。再听听他1979年为六位打击乐手所写的《时间机器》(Tempus ex Machina),22分钟长的曲子由轻不可闻的定音鼓掀开帷幕,未料出现的竟然是史蒂夫.莱希那般的错落节奏纹样,又像是荒郊乡野、雨声潺潺下的枯灯古琴,似乎依然和频谱关系不大。 格里塞接下来所作的尝试,一方面源自较成熟的声学理论,另一方面则源自工作室的技术手段。他这时在工作室的工作,意图进一步研究器乐与电子声响的衔接与平衡,试着超越施托克豪森与利盖蒂所掌控的“疆域”。格里塞曾盛赞利盖蒂、梅西安和施托克豪森三位是频谱音乐三位一体中的圣灵、圣父和圣子,我们起码可以这样理解,施托克豪森的观点“节奏是控制音高与音色之后得出的产物,音与节奏的关系是在音频构成要素的乐器垂直线,与推移整体音响形式的平行线作用的过程中展开的”对格里塞起到了启发性影响,使得传统音乐的要素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弱化——而让音色二字囊括横向与纵向的一切,包括多声部在纵向上的强弱比例;而利盖蒂又在《中提琴奏鸣曲》这样大量使用微分音的曲子(第一乐章“缓慢的歌”在中提琴c弦上走出了以五度比率为基础的和声旋律)中,对频谱音乐的风格成型又有着另一层面的推动作用。

此时此刻,为频谱学派提供了一定理论先导的另一位意大利作曲家塞尔西,正在巴黎狄德罗第七大学做着频谱分析。整个频谱学派中另几位成员包括梅西安的学生、受格里塞影响的胡雷尔(Philippe Hurel)、米哈伊(Tristan Murail),以及杜福(Hugues Dufourt)等等;与格里塞基本同辈的两位罗马尼亚作曲家如杜米特雷斯库(Iancu Dumitrescu)与奈米斯库(Octavian Nemescu)所进行的频谱探索,针对了“共鸣”产生的原理,也别有一番趣味。米哈伊在《Gondwana》里使用了钟铃这样非谐波频谱的乐器合成,而另外有些作曲家(如哈里.帕奇)甚至还特定为频谱作品设计一件专门的乐器。与频谱学派略有近似的还有,一位名为布莱恩.伊诺的英国人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研究的基于“波纹指标”的氛围音乐(如专辑《Discreet Music》)同样是由各种输入变量后声波的交错干涉构成的,没想到圈子不大,内部竞争还真是挺激烈的呢。 “用电脑合成出来的音乐都很难听。可能我们这些老耳朵还不能适应新音乐吧。实际上,我也试图喜欢过新音乐,比如用电脑重编的小号声,可是最让我讨厌的一点:是它们从不犯错,有理论认为,音乐的感人之处就在于那有一些错误的地方。伟大的女歌手唱歌也会走调。如果时时都唱得准确无比,就没有意思了。”这是意大利小说家艾柯曾经在书里的抱怨。他认为正是那种相对于标准的轻微偏差给了我们乐趣, 而电子音乐往往是精准的、僵化的,或者说包豪斯式的,太精准的演奏本身使调性音乐变测可控,传达的信息由此变弱。艾柯所说的并非没有一点道理。格里塞的最初听感,兴许会与早期施托克豪森的乐队作品(如《群落》、《方形》或 《混合》)有些类似, 不过肯定与当时活跃于法国的布列兹、泽纳基斯完全不同 。应当承认格里塞作品中所蕴含着私密化与高度的抽象性,同时还有一种莫名的幻灭感,让人联想到梅西安。然而,完全不似施托克豪森与梅西安的地方在于,他的唱片不会太挑战你的脑细胞,只需放松地听就好了。即使对高深理论的前提全无知晓,你我亦可充分享受其中,《声响空间》即是一个绝好的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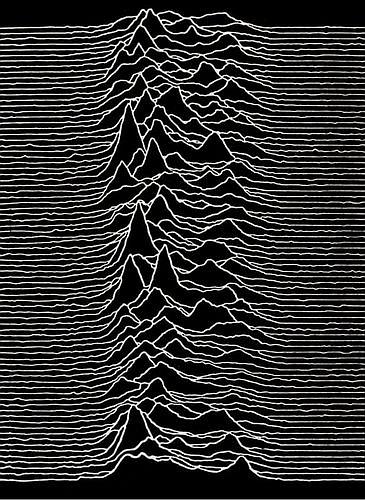
二
这部《声响空间》(Les Espaces Acoustique)是格里塞最重要、最长、且一直是研究者精力最集中的作品之一,1976年开始谱写,十一年后方告完成。它一共分为六个乐章,分别为: 《序曲》(Prologue) ,中提琴独奏,1976年 《周期》(Périodes),乐手七人,1974年 《泛音》(Partiels ),16或18人,1975年 《调幅》(Modulations),33个音乐家,1976-77年 《瞬变》(Transitoires),大乐队,1980-81年 《尾声》(Epilogue),大乐队,1985年 格里塞自己也承认《声响空间》是他“频谱音乐的实验室 ”,启发了日后的一系列进步。 Kairos厂牌下的双张《声响空间》,所附小册子挺“霸气”的,竟然全部法文,可见出版方不止一点点的自信,而这套确实是该曲最成功的演绎典范之一。Accord和Kairos这两个小厂,除非是常去法国的朋友,大都不太容易买到,国内订货也稍有困难。另外一个可选录音是 Accord厂牌下的,由法国Court-Circuit现代乐团完成,他们也是频谱音乐方面的专家。 第一乐章《序曲》就以中提琴独奏开场(担任独奏的是 Arditti Quartet的第一中提琴手Garth Knox),像从一个“小小的细胞”生长到了澎湃的海洋生物群落,而其高音颗粒充斥了微生物在显微镜下的触感和颤动,极端处略接近噪音,但依旧不失纯粹的色彩。格里塞极有设计感的想法在于,从第一首《序曲》到最后两首,编制从一把中提琴慢慢地拓展到了84人的大乐队,这一过渡与渐变的效果在那个年代可谓是惊世骇俗的(最终基本就是一大条“噪音曲线”了)。《序曲》据说还出过三个版本:中提琴独奏,用于声共振器和用于虚拟共振器的版本,后俩个在中提琴之外加入了五个附加的“共鸣体”乐器。
《周期》一段也是全曲最早完成的一段,也是全作品里最早让听众领会到早期频谱音乐激进和声效果的一段,可以想知,首演现场观众会如何地瞠目结舌。这里依照作曲家的说法,三种片段(紧绷、松弛与静止)分别对应于人类的呼吸─吸气、吐气与静止,它的结尾处,变格定弦后的中提琴独奏再次露面。 继而是导向下一乐章的连接部,乐队逐渐开始由低音乐器主导,与乐章开始出如出一辙。那种“人造和弦”的稠密再次出现。 而乐章的终结处是放慢的,鼓手在鼓面上轻轻拍拂,而其他乐手的低音量听起来多少也有点漫不经心,好像即将曲终人散。不过这是作曲家安排的戏剧假象,最后还是动用了整支乐队的力量, 用渐强至极端的骚动终结了它。 巨象的迈步开始了。写给18位演奏者的《泛音》开头,整支乐队在细节层面“动起了手术”。事实是:长号上的一个E音被拆解到了更细的组成部分,在各自的振幅上加以对比,交流。此时,基音反倒是最轻的,而第五与九级泛音较为响亮。器乐对长号的低音E进行模仿,实际上是建立在对声音进行声响频谱分析的基础之上——先将长号的E分解为它的多个泛音组成部分, 低音提琴开始从第三个至第七个E音(泛音)作周期重复,随即将其泛音分配到不同乐器上进行合成,当然为了乐器上实现起来方便,他尽可能地简化为四分之一或八分之一微分音。最终,乐队里每一件乐器都奏出低音E在自然和声频谱中的一系列频率。 这种用纯粹的器乐性音响模仿电子声学效果的方法,被格里塞命名为“器乐性合成”, 恰恰是那些频率交融成就了该乐章的声音个性。 开场处的声音有如来自远古的战场,低音提琴和大号等低音管乐器奏出大地开裂般的轰鸣,足以让人汗毛林立,到了乐章中段的长笛等高音声部,像是一个无数生物从缝隙里攀爬、飞跃与逃逸的“镜头”,乐章最后倒又像是细细的鸟鸣、溪流和树叶的摩擦声了。 在乐章的后半段的“稳定和声区”里,木管乐器如长笛和单簧管的交织非常惹眼,它们的合作既像是树林中的群鸟啼鸣,又仿佛对乐章的容量起到了某种扭曲与拉伸作用。容我揣测,此般和声组合大概可归入当代作曲“奇妙又不免带些诡异”效果的一个范例吧。听完《泛音》乐章,你大约会意识到格里塞的那句格言:“不再以‘音符’作曲,而是直接以‘声音’”并没有夸大。
不消多解释,为了完成泛音的细密分配,乐手听觉也必须超常地精细才行。据说格里塞能从第一个基音一直听到它的第11个泛音,可见他谱曲时“戴着”一副什么样的耳朵!自然没法保证人人都如此,所以有港台乐评家坦言:要用传统乐器合成出如此精密的演出效果(有时谱上出现繁多的指示),所付出的精力无疑数倍多于简单地用电子合成器完成任务。事实上,当一个繁复乐段一定要用真实器乐奏出时,演奏家敏锐的听觉也可能不够用,即便演出复原度再高,很多时候,器乐的分辨能力都一定没法细腻到与创作思路全然一致。其实这在频谱音乐中也是挺常见的,行话称作“变形”或“不统一”尤其当乐器众多时,人之感性与理性二者往往会形成了奇特的混搭效果,而对它们不规则的摇摆偏差的预知, 也会成为他们谱曲时所关注一大要务。这恐怕也是为何从一开始,频谱乐派的作曲家们就倾向成立专属乐队,便于随时密切沟通。 第四乐章的编制发生了较大改变。唱片中作品二、三乐章的演绎者都由小编制的阿斯科室内乐团(Asko Ensemble)完成;而第四乐章《调幅》开始之后的乐章都是是科隆的WDR交响乐队,尤其在铜管乐器声部上呈现出教堂应答圣咏般的风味,又在某种程度上像与老师梅西安的《图伦加利拉交响曲》里那听得人手足发麻的铜管,遥远地交流着什么。 庞然大物般的《瞬变》出现了,它开始蜿蜒地行进,向高潮踱步....这简直是名副其实的“渐变”,而不是什么“瞬变”!大乐队部分让我不自主想起了瓦格纳手底的序曲合奏写法,多少像是个古怪的巧合。之后,长时间孤独着的打击乐手再次高举起了手中的钹,低音提琴上无限重复着和弦——乐队则在各种频率上模拟着之。 由于用到了全编制88人的乐团,作曲家能在谱中逐步加入更复杂而新颖的泛音组合,据说《瞬变》的顶点时分已用到了E音的第55个泛音,难以置信。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格里塞在最后两个乐章里都用了电吉他的拨奏(他早期的《漂移》里也有电吉他),那种凛然的效果就像乌云压城, 古拜杜丽娜的那首《时间形态》(Zeitgestalten,1994年)不也是让电吉他成为了主角吗? 最后一曲《尾声》里,你会感觉再次进入了某种混沌状态。音乐的复杂织体,又一次被削减到独奏中提琴上,将作品开场主题再现。不过这次它的形式有些支离破碎,四把圆号进入(独奏部分由澳大利亚圆号手Andrew Joy完成),他们吹出的调子有如进入了黑洞,歪扭而模糊不清。曲子就在这样一种了无声息的向内塌缩中走向终点。我在猜想,现场最后一个音符落下后,会是什么样的感觉。据说,科隆演出时最后灯光聚于乐团手上拿着钹的打击乐手,作势要大声击响,观众屏息,音乐结束。 纵观全曲,格里塞的用意大约在于将乐曲中的泛音在一个一个拿掉,这未尝不在暗示着一次从无垠大的宇宙回到"一”的归途,而返过头看,那第一声不太响却斩钉截铁的中提琴,是不是在仿效着上帝的第一声言语:“要有光”呢?
三
爱因斯坦当初都认为太过微弱而无法探测的“引力波”之声,如今听起来就像啾啾的鸟鸣。 尽管有人觉得来源于误差,人类还是在2015年9月宣布首次“观测”到开启了天文学新时代的“引力波”——其实从更准确意义上说,是收到了某个富于意义的声音频率信号。两家天文台的众口一辞:“GW150914引力波事件,图中显示该频率在0.2秒的时间内从35Hz横扫到了250Hz。”该信号在理论上应该来自于黑洞互相绕转、并即将合并前的最后阶段,所以它的出现验证了广义相对论的准确性与黑洞的存在,而早期宇宙量子级别的振动奥秘,从此并非是人类不可能捕捉之事。 这件事倒从另一角度提醒了我们“仪器”对于声音分析的决定性帮助。众人皆知,声音有着四大物理特性:音高-对应频率;音强-对应振幅、音长-对应时值、音色-对应谐波成分与发音过程。在频谱学派那儿,分析仪一类的工具,将声音波动自动分解,省去了第一步骤需要用人耳辨别的高难度麻烦。 既然频谱图能事无巨细地显示出这些要素,那么频谱作曲家就可以将声音分解析出频谱成分,令其进一步成为作曲的依据。 前文已提到,格里塞用了电子声像仪(一说声谱分析仪,但应属同种)分析了长号上低音E的频谱并改用音高记谱,于是获得了用作基础标本的泛音序列。
分析准备期里,频谱作曲家常用快速傅里叶转换法,傅里叶转换法最早在19世纪提出,认为声音都可以转换到波形,且是最简单的正弦波的集合体,所以该方法实质是将一个信号分离为无穷多多正弦/复指数信号的加成 。而真正到了谱曲阶段,频谱学派的做法严格地说也属于“算法作曲”范畴。二十世纪兴起的所谓“算法作曲”往往是立游戏规则在先,对主题动机进行各种发展变形在后,有人认为莫扎特的《作曲骰子游戏》就是第一部算法作曲的实例,因为莫扎特建议演奏者以掷游戏骰子的方法,将预制的那些短小动机与表格序号一一对应,然后进行拼接成一首小步舞曲,想法煞是有趣。这类貌似基于冷冰冰技术流的频谱学派做法与战后流行的简约主义完全不同,但每当格里塞的音乐由传统乐器奏出,却不可思议地产生了令人刻骨铭心的电声效果,在听众的耳里并不比简约主义更难接受一些。实际上,格里塞认为,频谱注意最终的目的是实现时间的完美整合,在更大程度上,他们想要的是将那些微分效果整合成一体化的流动色彩音响,而不是对细节的吹毛求疵。 还别说,“引力波”启示了一件更重要的事,即本唱片之标题:“音响”与“空间”之间所产生的亲缘关系。对于毕达哥拉斯时代的人,音乐和数学(更确切地说是算术)本就不可割裂——它们都体现了天地宇宙的和谐运行,无论是音符还是数字,俱是打开自然宝库的钥匙。格里塞说他自己毕生都在美学疆域探索音乐与时间的关系,可其实 “空间”与音乐也是唇齿相依的——振动与频率常常能从最细微与视力不可企及的角度,反映出一个陌生宇宙的纵深与秩序,不是吗?哪怕以最浅表化的目光度量,一件乐器(如在《序曲》中)也好,多达84件乐器(如在 《瞬变》里)也罢,都被安排得如此井井有条,宛若星河运转之秩序井然,本身已经是一桩令人讶异的事情了。《音乐声学与心理声学》(Howard和Angus著,陈小平译)之作曲算法与算法作曲一章里就认为:“早期频谱音乐让听众游弋在时间坐标中,模糊地感知音响的结构”;而杨珽珽的论文有着别出心裁的视角:“从《序言》至《尾声》 ,是一个从音色到强度都不断增加的,每一首作品的结尾都是下一首作品的开始,类似中国传统的‘鱼咬尾’,体现了一个循环而整体的设计。” 回想一下,发觉物理“弦理论”所主张的,宇宙万物均由振动的“能量弦”为基本单位组成,而新的一套“圈量子理论”则认定,宇宙的大网实质上是无数的“环圈”(环圈的大小和弦理论里的弦的大小一般无二)。既然不是“弦”就是“环圈”,振动时的各种声响你我曾几何时侧耳倾听过?还是说:时时都置若罔闻? “宇宙中最不可理解的事情就是,它竟是可以被理解的”——这句,当真是爱因斯坦最严肃的一句玩笑话。自格里塞开始,不管是闪烁的音色,密集的纹理,还是自然、人造二者的色彩混搭与对共振、周期概念的执着,频谱学派皆为世界提供了一套令人兴奋的宇宙秩序观。

四
有人对第八首《尾声》受尾持有异议,觉得如果格里塞直接用《瞬变》作结尾是个更完美和俯瞰全局的做法。真的如此的吗?这也是我希望读者亲自听过后,留出的一份思考。 初听时你可能会以为,《音响时空》里的一大部分比重,不都是由飘忽不定的、分层次的嗡嗡的金属鸣响组成的吗?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声音在不知不觉地流动,它偶尔爆发出的不稳定火焰,亦或更经常陷入的、空无一物的寂寥之间,你会恍惚察觉时间-空间二者正在默默地转化,转化过后得到的呢,怕是早已远离我们所熟悉的生活尺度。作曲家的格言是:“目的与过程是相似的东西,目的是过程的收缩,反过来过程是目的的扩张。” 《卫报》专栏作者塞尔维斯的一篇短文里,还举荐了格里塞的另外三首佳作:《时间的漩涡》(Vortex Temporum),它的开头部分格外让人惊诧 ,乐队音响将最初产生于钢琴键盘上的盘旋音符扩大与延伸化,主题基于拉威尔的《达芙妮与克罗埃》里的长笛独奏;为室内乐队、打击乐和电子合成器所写的《时间与泡沫》(Le Temps et l'Écume,同样是在Kairos卖得不错的一枚) 算得上他在标准“闪烁和声音色”以上的一个超然存在,带领你“不安却震动地穿过一面镜子”,而这面镜子像是丹麦童话里才有的东西,一端连接着所有的表象,如尖锐鸣响着的木管声与一段小号独奏,而另一端则通向意欲气吞寰宇的乐队和弦……作曲家逝世之前所写的《四首为了越过临界值的歌》(Quatre Chants pour Franchir le Seuil),沉思感甚强又清幽如魅,堪比黑洞效果的打击乐声部——几乎能将整个世界都给吸进去,声乐部分则比较亲切,结尾处的歌词开放度极大:“我望着海的天际线,这个世界.....”。这些作品似乎皆在暗示,乐谱上的“小蝌蚪”并不能代表格里塞想要的声音效果的全部!你讶异地发现,与刺耳音高并生的是超出想象力的音响色彩层次,宛如一台砂砾与牛奶相糅杂的宴席。再补充一句:声乐元素在格里塞的作品里一直不多见,该缺憾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才被弥补,那又是新一轮的脱茧而出。
对于没有站在学院作曲前沿的普通乐迷,或是从未接触过类似音乐的人而言, 它们本身已意味着一个奇想的世界,更加不用说在频谱乐派后期又出现了基于算法的“自动作曲系统”(一个争论不小的话题)。有趣得紧,当格里塞宣称道:“我们是音乐家,我们的范本是声音,不是文本、数学、戏剧、视觉艺术,更不是原子物理、地质学、天文学与针灸穴位,都不是......" 他的音乐却像是一次又一次地在质问着:古老的音乐传统惯例是否专属于某一阶层和人群?比如音乐家?而声音的本质到底又是什么? 起码,《声响空间》这枚唱片像是给了我们一个浮想翩翩的答复。我们开始从冰冷、客观的声音的物理性质思考作曲这件事本身。就起源上讲,这种“格里塞音效”来自于程式化的声学及心理声学理论,却在我们耳朵的实际听感中取得了很强的可信度,不是一件在传统作曲语境之下很难以置信的事情吗?换句话说,他们基于数学层面,近乎奇迹地维持着一种从巴赫、勃拉姆斯所传递下来的“自然有机体”属性,而非是想象中拒人千里的冰冷与客观。因此格里塞的音乐与布列兹、施托克豪森都存在着方向性上的差异。同样是对声音细节的构造,布列兹或贝里奥时常会刺激你的耳朵,而格里塞的这首,我以为应该不会,只因《声响空间》 上空笼罩着那层有温度的“光环”(称之“灵光”亦可) ! 这不正是频谱学派能不落机器性窠臼的优势所在吗?那么如果进一步问,到底置入几许的人性温度,或者说多少的比例才是最恰当的?我有时真觉得,频谱学派不经意捎出些许个严肃到有点残酷的话题。
在格里塞生活的那个时代,频谱作曲家们并未狭隘地一味强调“一切为物理特性服务”。换句话说,他们的创作思维中,“以声音自身”为本质只是一种态度。某些意义上,最初频谱音乐的出现,是为了在过于注重“抽象规则”的序列音乐与音响性能强但不怎么有“规则”的电子音乐找到一个融通的缓和带。既要摆脱调性束缚,又需摆脱无调性的束缚,想来想起只得回到声音振动的机制本身。这也确实是可行的,不过那样的原理研究终究是途径,而非目的所在。最终,好的频谱音乐应如的某种“生命体”,通过展现时空的潜在关系,让音高、旋律与和声的替代品——频率与频谱,成为宇宙中固有与未知声音的另一类解释方案。杜福在一次讲话里就说得很明白,大意是频谱音乐是希望在序列音乐开创的道路上更进一步,变得纯粹透明,但与序列的截然不同之处在于:“序列依靠乐音的堆积与部分的解决来获得张力或降低音响冲突,而频谱音乐则主要依靠声音内部结构变化,如包络关系的改变,泛音比例的扩充压缩等手段获得色彩”,笼统地说,序列是反听觉心理学原则的,因其驱动力来自隐蔽的多项要素,在创造非线性有序结构的同时,不免会打乱自然感和人性化。但频谱作曲家们仍坚守着乐曲的线性与整体感,秩序结构是外露的,频率关系的统一也是符合心理声学原则的。第一批频谱作曲家的导师与前辈,恰恰都是他们将与之对抗的序列主义大师。假使说勋伯格是对浪漫主义的反叛,布列兹是对勋伯格的反叛,频谱音乐不出所料地成为了一次对布列兹序列主义的反叛, 那么未来的数年间,会不会由一批新生代艺术家唤起对频谱的又一次新反叛呢?
如今在国内,且莫说频谱音乐,就是微分音演奏的系统训练也很匮乏,主要仅有一本加思.诺克斯的《中提琴空间》(Viola Spaces,为今井信子而作)作为教材。毕竟,在实际演奏微分音时,习惯传统弦乐教学法的乐手们需要不断调节听觉与手指触点,如若技术不达标,将频谱的理论一层贯彻到位貌似就愈加之困难。 如果读者还有兴致,可在缪萨《二十世纪音乐》一书里为格里塞与同道中人米哈伊等人的立足风格寻觅到更详尽的解释论据,例如:
“作曲家先对声音频谱进行人工复制,将泛音分配给不同乐器,然而让它们各自发生时间和空间维度上的渐变......摒弃所有将声音抽象化的方法(包括数学),换句话说,纯形式,纯抽象的音乐规律与逻辑,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反倒是感知力层面上的具体参数,演化出了一套有内在逻辑的作曲程序。不过这样的音乐效果,也有着一个不可避免的窠臼。框架往往是赤裸裸的,仿佛刻意营造出一种透明风格。这一点,也是它区别于十二音体系音乐的另一个显著特征,虽然很看重音色,但更加重视整体音乐形象。复杂的音色是音乐风格的轴心。”
1998年,格里塞辞世。记得笔者当初读到《汉书•艺文志》所言“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然星事凶悍 ,非湛密者弗能由也”时,颇感惊讶,以为星事顶多只是扑朔迷离罢了,何道“凶悍”?后来才理解了下面一句的补释,因为当时负责“星事”的官职要用星事来谏上,故而是冒着风险的。远在西方的格里塞大抵是不懂得东方这层典故的,可是他的一批创作分明能借着对宇宙秩序的重整而直抵湛密之府,全然不顾会引起听者与评论家怎样的震惊。如今在他逝世二十余年后重品《声响空间》,我们承认得加上一条:大概格里塞真是能从星云崩解中一睹爱与永恒的那个人。
附注:
1)A guide to Gérard Grisey's music(Tom Service) https://www.theguardian.com/music/tomserviceblog/2013/mar/18/gerard-grisey-contemporary-music-guide
2) 由于对作曲不是太熟悉,文章中的资料来源方面,还得感谢李鹏程、代博与汤涟漪几位老师的拨冗指点。
2017.4
投稿、挑错、建议、提供资料?在线提交
推荐 Recommend
用户评论 Reviews [ 发表评论 ]
| 快来抢占沙发吧! |
